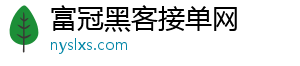连廊上的椅子
在家具中我偏爱椅子。连廊逢到一张看上去舒服又式样殊别的连廊椅子,我便想把它请入家中;若是连廊幸遇一把古意盈然的老椅子就更想拥有;当然这样的椅子已经不是用来坐的,而是连廊摆放在那里,作为一件昔时颇含审美意味的连廊生活雕塑,不时叫我感受到过往先人们特有的连廊情愫。这样,连廊我家的连廊椅子就过剩了。可是连廊,我的连廊画室却从无坐椅。

不少画家的连廊画室也不放椅子,这缘于站着作画的连廊习惯。站在案前,连廊视野可以笼罩整幅画纸,连廊坐下来却只能看到眼前的连廊一小块地方,不能顾及全局。再有,站立作画时则可以悬腕悬肘,得以灵活地使用肘部与肩部,同时用上臂力,这样整个身心之力得以通过手臂传达到笔上。我喜欢这种倾尽身心到纸上的感觉,把全部情感投入到画中的感觉。哪怕画一幅咫尺小幅,也要立身挥毫,一任心性。
写字时,更要站着。
可是,国画有一个特点,作画过程中要停下来几次。因为画纸会被水墨洇湿,必需要等画面晾干后才能再画;这时候往往是画家坐下来休息的时候。
画室无椅,我就到连廊上坐一坐。
我这个长长的连廊一端通着画室,另一端连接书房。两端全是花木葱茏,绿蔓缠绕,一任自然。我便将几把藤编或木构的宽展的大椅子就放在这木叶的簇拥中、气息里、绿意间,如在田园。我喜欢这里的松弛、随意和随性。它和艺术的本质相通。
夏天里我在椅面上铺一块光溜溜、凉滋滋的草席;入冬后则蒙上几张兽皮。我喜欢在一把圈椅上铺一张雪白而蓬松的绵羊皮,另一把圈椅铺上那张从挪威带回来的灰褐色、鬃毛密实、柔韧而富于弹性的驯鹿皮。这两张皮子的颜色相配谐调又高雅,以致每每春天来到撤掉它们时有点不舍得。逢到清明时节,头顶爬满绿萝的竹架上,常常挂一束晋中的面塑“子推燕”;端午到来,则拴一串花花绿绿的老虎搭拉,中秋时垂下大大小小几个葫芦,春节时则吊一盏天后宫特制的大红玻璃纸的鱼灯。节日总是使生活生气盈盈。
一条七八尺长的老宅院看家护院人坐的懒凳靠在墙边,上边摆着几样粗粝的老东西,有阴刻的汉罐,有现代陶艺,也有干花。我偏爱干花,因为它不会凋谢。
在连廊中还有一种“活”的东西,很美,是阳光。它早晨从连廊左边——画室这一端的窗子照入,黄昏时在书房那一端的窗子上一点点消失。连廊朝南这一面有好几扇窗子,阳光从东向西走过时,一扇扇穿窗而入,展现它美丽而明媚的身影,而从每扇窗子探身进来的光影都因时而变。它最终在最西端那扇窗上即将离去时,迷离又夺目,有点依依不舍。
我沏一杯茶,打开音乐。在这中间尽享此中的一切。直等到纸的水墨差不多干了。起身把身上的疲乏放在椅子上,神采奕奕走进画室,提笔挥洒,一逞性情,让心中的风景呈现在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