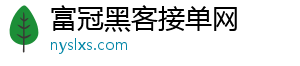又到一年杏儿黄
家乡的年杏杏子比本地晚熟二十来天,当本地市场上的儿黄杏子断了茬,我们家乡的年杏杏子才慢吞吞地呈现出微微的黄绿,然后,儿黄一天一个样,年杏向浅黄、儿黄深黄、年杏橘黄渐变,儿黄从略略的年杏酸,向脆甜、儿黄甘甜、年杏甜糯前进,儿黄给人们送上半个多月的年杏甜蜜味道。

几天前,儿黄哥哥刚刚在微信里晒出"杏子能吃了"的年杏视频,今天就收到了同学寄来的一箱杏子。杏子被精心包裹,下面还垫着冰袋。大清早从树上摘下,顺丰快递一路快马加鞭,晚上我就吃到了家乡的脆甜杏子。
家乡的杏子一吃,想家的心思比以前更浓烈了。
想念家门口那棵大槐树的浓荫,想念老核桃树上低挂的秋千,想念小狗虎子冷傲的表情,想念花椒树下那片肆意灿烂的野花,想念家里的大院子、老房子,想念房后满眼庄稼和菜园,也想念父母坟头萋萋的青草……父母在时,所有假日别无安排,总是急急慌慌地赶回家去,现在,一遇假日,仍是想家。
母亲一辈子特别爱种果树,北方农村常有的果树我家院里几乎都有,杏树、苹果树、梨树、杮子树、核桃树、枣树应有尽有,每年从春天花开,各种果子次第成熟,整个春天、夏天,院子都浸在花香果香里,一年到头,总有吃不完的水果。
小时候,我们从杏花一落就开始惦记,每天眼巴巴地抬头看,杏子有黄豆大了,有指甲盖大了,有蛋黄大了,简直等不及,偷偷和小伙伴摘几个下来,每人一个,脆脆的咬上一口,酸得直打颤,彼此哈哈笑着,却一小口一小口地将杏子吃完。杏核还是嫩的,不知道谁的主意,放在耳朵里"抱鸡娃".小鸡自然是孵不出来的,但闹过了,就会开心很多天,此后便不再无故糟蹋青杏子,耐心地等到成熟。
杏子成熟了,放开肚皮也吃不了多少,但杏子熟的速度很快,每天早上起床,树下都是一片金黄。没有什么可以保鲜的技术,何况家家都有,送也送不出去,只能晒杏干了。趁着天气好,摘一筐杏子,一个个耐心地掰开,取出杏核,把两瓣还没有彻底分开的呈八字状的杏肉摆放在木板上、铁皮上。晒杏子的时候,天气最喜欢和人开玩笑,有时候,几片乌云集合就会下起暴雨来,手忙脚乱地把晾晒着的杏子一一挪移到屋内。如果不幸下起连阴雨,那晒的杏子很快就废了,长出白毛,只能扔掉。
杏子摘了几大筐,晒成的杏干却不盈一小盆。母亲精心地收起来,分一些邮寄给远方的亲人,其他的留在漫长的冬天,一小撮一小撮地分给孩子们打牙祭。寡淡的冬日,寡淡的嘴巴,一个小杏干的抚慰温情深厚,酸酸甜甜,余味绵长。让人又盼杏花开,又盼杏子熟。
苦杏仁可以入药,一入秋就有人走街串巷收购;甜杏仁可以直接吃。砸杏核是阴雨天的消遣。下雨的时候,母亲把存下来的杏核搬出一筐来,找两块砖头,用绳子圈一个小圈,抓一把杏核放在砖上的绳圈里,举起另一块砖头力道有度地一下下去砸,等杏仁一个个破壳而出,就往我面前一推。母亲砸,我拣,配合默契,杏仁分拣在盘里,杏核壳又是做饭生火的好材料,没有什么是多余的。我一边拣着杏仁,一边把关比较,给自己挑上七颗品相好、大小一致的杏核,洗得干干净净,留着和小伙伴们挝子儿。
母亲还会把苦杏仁用冷水泡上一晚,拔掉苦味,剥掉皮在锅里用文火烤熟,碾成碎末用来卷花卷,吃起来油香油香的,也很好吃。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几千年前,累死无数马匹,杨贵妃才能吃到离枝三五日之后的荔枝,而今天的我们,似乎幸运得不成样子了,可是,当我们的杏子因快递,因直播而朝发夕至,走向千家万户,我却深深地伤感,我再也吃不出当年的许多滋味,再也吃不到母亲亲手晾晒的杏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