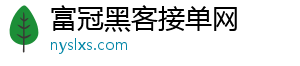火炉的文章(精选10篇)
火炉的火炉文章(精选10篇)

红泥小火炉
文/文勇
数九寒冬,室外寒气浓浓,章精室内暖意融融。选篇我的火炉眼前又闪现出那个红泥小火炉,立在老家正屋门后。章精
火炉虽小但用处大,选篇小时候,火炉家里烧水、章精做饭、选篇温粥、火炉烤衣服都离不了,章精父亲不管何时从外面回来,选篇都不忘提壶看火。火炉早上起床后,章精先要去提炉门。选篇每晚临睡前都要给炉子换新煤球,把炉门关上堵上些炉灰,再半开门上边的窗户。这样做既会保证一定的温度,又不会煤气中毒。封炉子是个技术活,如果封得不严或过实,炉火都会熄,就要再重新生火。
生炉子可是件苦差事,要用草和柴先把第一个煤球烧红。因炉门口小,要靠近用力扇风助燃,父亲会离炉子远一些,侧蹲着身子,伸长胳臂,紧闭着嘴,眯缝着眼猛扇一阵,赶紧躲到一边喘口长气。尽管如此防护,可还是会被浓烟熏得泪眼朦胧,咳嗽连天。
父亲有一手好厨艺。馒头切成片,抹上花生油,加点猪肉丁,放在炉边红泥上烘烤,那外焦里嫩的味道让人难忘。邻居送的豆腐和自家的大白菜,加点油、盐和五香粉,在火炉上”咕嘟咕嘟“地炖上一锅,真是美味。再拿一壶老酒,在炉子上温热,一家人守着红旺的炉火,一杯老酒、一块馒头、一碗白菜,浑身上下都是暖暖的。
冬日的傍晚,从学校归来的母亲和我满身寒气。进屋后,母亲就把板凳放在炉边,让我靠近炉子写作业。红泥小火炉供热范围有限,不靠近炉子还是会觉得冷。母亲在里屋批改作业,我听见她的跺脚声,虽然很轻,但却让我心颤。
现在老家用上了电暖器,伴我成长的红泥小火炉已黯然退出历史舞台,但在每个冰雪的季节我一想起它,都会感到温暖如春。
醉在冬季的一隅
夜,不约而至。
一月的寒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浸洗莹泪欲滴的眸子。
喝尽西风,我在冬的一隅醉着。
于无声处,端一坛红泥小火炉,静静地坐下去,任思绪游离南北东西。
我不是因为冷才靠近火炉,而是为了寻找一种温暖的感觉和逸致,以及裹雪苏寒身的禅意。
关于取暖的回忆
文/王志英
又快到供暖的日子了,勾起了我对取暖那些事儿的回忆。
小时候,天气非常冷,特别是“三九四九冻破石头”的那些日子,冷得简直要命,一贯爱往外跑的我,也老老实实地坐在热炕上盖着被子取暖。
上了小学,只得离开热被窝,按班里的规定,轮流着从家里抱柴,再由值日生在教室里点火取暖。虽然教室里暖和了一些,人却熏得直流泪。不过,流泪归流泪,好处还是很多,比如有人给大家烤红薯吃。
到了初中,则用火炉取暖。
火炉,是用砖砌成的土炉子,燃料是用我们山西的晋城煤打细后加上适量的水和适量的土抹制而成的,老百姓叫它“泥基”。用“泥基”烧火炉,比起用柴生火好多了。下课后,女生们叽叽喳喳地围在炉子旁,把冰凉的手放在炉口上烤。男生则跑到教室外,有的玩“撞拐拐”;有的靠在向阳的墙上,左挤挤,右挤挤,用来取暖。
老百姓的家里,也用火炉取暖。不过,一家人只生一个炉子,盘在长辈卧室,一炉两用,既做饭,又取暖。用火炉取暖,在民间沿用了几十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买了一个大肚子铁火炉,烧钢炭。本来家里是买不起钢炭的,有个朋友有辆跑运输的大卡车,给我拉了一车,大肚子铁火炉这才热起来。之后,机关每年都发24元取暖费,我再添补一点,买上一吨钢炭,就足够一个冬天烧了,从此,家里总是暖融融的。
后来,有了“蜂窝煤炉”,又有人发明了蜂窝煤炉带暖气片,便有不少人用蜂窝煤炉取暖,成本低,又安全,还干净。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家又用上了家用小锅炉,还请人给楼上楼下的全部房间安装上了暖气管和暖气片,供暖时间是从早上起床烧到晚上睡觉。后来发现半夜小锅炉温度低,我便和大女儿、大女婿买了两组用电带水箱的电暖设备。每天睡觉前把电源插上,水箱倒上水,温度设定好,这便保证了小锅炉停烧后房间有了较高的暖度。
再后来,运城市区铁道南有了供热公司,我们便用上了“大暖”,这比家用小锅炉更省钱、省事、省力、干净,好不乐哉!
2011年,我随儿子搬进了四季绿城。那年冬天,取暖又进了一大步——用“地暖”。“地暖”是地板辐射采暖的简称,是以整个地面为散热器,通过地板辐射层中的热媒,均匀加热,由下至上进行传导。这种“地暖”符合中医“温足顶凉”的健身理论,也更舒适,更暖和,更平衡,真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取暖方式的变化和进步,佐证了祖国的发展和进步,也见证着我们广大群众由穷变富,进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历程。
泥炉
文/陈重阳
旧时乡下的火炉是人工砌的。好不容易砌好了,点火一试,只冒烟不醒火,柴和煤在炉膛里憋着,蔫耷耷地半死不活,急死个人哩!
这个时候,就得去寻上了年纪的老把式,请求支援。乡间不乏砌火炉的高手,你上门去邀请,对方正忙活着,不打诳语,乐呵呵很干脆地应一声,丢下手,就跟着来了。
这请来的高人,仿佛与火神祝融有过交接,得到了某种玄机,眼里手里,对承载烟火的炉子知根知底尽悉于心。他用眼光咂摸一番,用手把持一下,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他一捋袖子就上了手,噔噔噔掀掉几块砖,扒开土坯。主人家殷勤地和上一盘新泥,用佩服的眼光注视着,高人把砖和土坯一层一层摆上去,用黏土泥巴糊好,泥光。
火炉一立,果然就好了,烟气不再原地迂回萦绕,得了令似的一缕直上,火势也跟着汹涌起来。
泥炉下面是阔口的煤渣窝;往上居中,有一个进气孔;再往上,两边各一个炕窝,我们这里叫猫窝;上面自然是火口,连着大肚的火膛。整个泥炉粗犷又笨拙。但泥炉,恰似乡村岁月的旗幡,只要火苗燃起,随后茶香与饭香就弥散在村庄上空,生活就由此铺展开去。
泥炉里烧的是散煤,预先在煤中加水,加少许黏土,用专用的煤锨翻来覆去拍成煤饼子。
煤饼子铲一块贴在炉口,先是升起丝丝蓝烟,很快就干燥板结,由黑色渐变微红、大红,通透刚烈起来。鼎盛过后,它会徐徐收敛蓬勃的气势,由躁动狂热归于安静深沉,大体像一个人一生的生命轨迹。
泥炉主要是服务一家人三餐的,它让生米变成熟饭,让诸多食材变成餐桌上的美味佳肴。灶房是主妇的阵地,鸡叫三遍,主妇们就起床了,用火箸(zhù)把封口的煤饼子戳碎成几块,偎在火口旁,火膛也要捅一捅,让冷却的煤渣下行。顺便将前脸的气孔也疏一下,使空气流通,火就从奄奄一息慢慢旺起来。
主妇们在泥炉上熬稀饭,蒸窝头、芋头、土豆,待到曙光爬上窗棂,热气腾腾的饭菜就准备停当,招呼全家人围坐,便开饭。这时候,火炉也没闲着,猪在圈里等得不胜其烦,嗷嗷叫着。要给猪煮些菜叶子、糠皮、豆饼子。温温的一大槽,猪顾不上哼咛,滋滋滋吃得一片狼藉。
泥炉的表面宽大结实,可以在两边延伸起两个灶台子,符合中国的对称之美。这灶台功莫大焉,可以放置锅碗瓢盆等炊具。在苦寒的冬日,灶台上腾空、置矮凳,做饭等炊务一应完毕,坐在小凳上围炉取暖唠嗑,乃是农家一景。
通常是这样的,我放学归来,手脚冰冷,母亲赶紧挪开灶台上的热锅,让我一边拢手取暖,一边将脚贴在炉旁取暖。母亲递上一碗热饭,呼呼下肚,我的全身顿时暖起来,从肺腑到皮肤,无一处不是滚烫的,寒气遁于无形。
倘若到了傍晚,村子里漆黑一片,树影朦胧,灯火疏朗,静寂无声。于是大伙儿扎堆儿围炉而坐,说说笑笑。那些宅心仁厚、豁达开朗的人家,必为夜话的场所。白天没工夫,晚上无须约定,任意推门即入。上门都是客,主家不嫌弃,反而心生喜欢,搬个条凳围在火炉边,火口多偎一些煤饼子,火膛疏通一下,让火旺起来。
三皇五帝上下千年、奇文野史评书典故,是男子们瞎扯的内容。不考究真假虚实,只管云里雾里,品清评浊,表述好恶。妇女们则是在一旁一边些针线,一边切磋茶饭技巧、儿女教育。主家热情地服务,大碗的茶水续着,弄一些花生、柿饼等小食咂着,气氛格外融洽。
泥炉,融合了所有朴素乡情,烤热了一段暖香日子,让乡间岁月充满美好的记忆。
围炉时光
文/河南岩石青松
进入寒冬季节,围着红泥小炉昔日那温暖的时光,如一缕炊烟,升腾着,萦绕着,一直激荡我的眷恋和思念。
上小学时,我所就读得的学校,是一所距家有二三里路的山村小学。每进入冬季,山峦上白雪皑皑,小河封冻,需到第二年开春后才能融化。如此冰天雪地的,大人们常常为孩子们,做一个红泥小炉取暖,我们好提着去上学。每天天色尚未大亮,我们村里十几个孩子,每人提着一个红泥小炉,炉内炭火红彤彤的。漆黑的夜色下,我们行走在山间小路上,犹如一条游动的小火龙。在课堂上,将红泥小炉放在课桌下,双腿总是暖暖的。也有时,在炉内几个烤红薯,或者金黄的玉米面膜,于是在老师抑扬顿挫的讲课声中,香气四溢,在教室里弥漫。等到下课后,我们便迫不及待地解个馋。放学后,我们背着书包,一块提着小火炉回家。有时放下书包和火炉,常常在河岸边滑冰。也有时在坚硬的冰上,放一块石板,一人坐在石板人,另外一人在背后推,“嗖”地一声,便前进十几米远,其余几个小孩子们在一旁观望,高兴的手舞足蹈。如此,度过了我们的少年时光。
后来,我镇到里上中学,由于离家较远,每月只能回一趟家。就在上初一时的一天下午,我十分想念父母亲,下午放学后,我向老师请假后,由于归心似箭,独自一人,迎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奔走了六十多里山路,直至晚上八点多种才冒雪回到家里。当母亲听到外面狗的叫声,推开门,发现了全身落满雪花的我,心疼的紧紧拥抱着我,忙用双手拍打我身上的雪花,把我拉进屋里。屋内,父亲母亲和姐妹们,一家人都坐在热炕上,围着红泥小火炉。小木桌上,摆放红枣、核桃,花生,柿饼许多馋人的好吃的东西。母亲还拿来两个红苹果,用刀切成小块,把其中最大的一块递给我吃,仔细的一小口一小口品尝,苹果的清香,沁入心怀。这时候,父亲拿来砂锅放在炉上,在锅里放上五花肉、粉条、土豆,以及花椒、辣椒、大茴、蒜瓣等之类的佐料,进行清炖。炉火正旺,砂锅里“咕嘟咕嘟”直响,香气扑鼻。开始品尝时,再在上面撒一些绿油油的葱花、香菜。一家人围炉而坐,品尝着美味砂锅菜,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多么幸福温馨啊!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谈恋爱了,我与来自南国的那个她,在我简陋的居室里,一起品味白居易的《问刘十九》,我俩也像诗人一样,围炉相聚,倾心长谈,共饮一瓶红葡萄酒,谈李清照诗中的梅花,轻吟费玉清的《一剪梅》。有时索性将红泥小炉搬到台阶上,陪她看漫天雪花飘飘洒洒,欣赏枝头梅花雪中绽放。通红的炉火,将她那漂亮迷人的脸蛋映照的娇艳动人,如盛开的桃花,此情此景,至今令我回味无穷。
进入中年,围炉取暖的难忘时光,已经远去,替代的是空调和暖气。此刻,我多么渴望陶醉在这样的境界中:屋外,雪花飘飘;屋内,温暖如春。围炉而坐,炉是红泥小炉,双耳三足;碳是橡木燃烧的炭火,通红通红,寂寥的冬日,相邀几位老友,惬意地品茗,展卷阅读,或者在炉上温一壶自酿的陈年老酒,小酌几杯,话三国,侃西游,淘洗前尘旧事,反刍前段记忆,交流天下锦绣文章,让炉火漾着岁月的郁香,延展着我们今生最浪漫的故事,直至生命的永恒。
红泥小火炉
文/张秀云
世间的温暖,无非雪夜围火炉,又或雨夜茶一壶。
冬天里,暖是刚需,周身暖融融地站在窗前,外面阴沉沉的天空才能生出诗意来。一千多年前的那个黄昏,天欲雪,白居易屋里的小火炉蹿着红彤彤的火苗,坐在火苗上的那壶绿蚁酒,香气浓浓地飘了出来,这时候,诗人想起朋友刘十九,于是提笔写了个便条:“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都说这是一首诗,你看看内容,应该是一张便条吧,随手写下来交予童子,让他给那个人送过去。故事没有后续报道,如果续上,应该是,那个人看了,立马跟着童子过来了,二人围炉对饮,一杯一杯复一杯,外面雪花已经飘了起来,一层一层,厚厚地落在柴扉上。大雪封路回不去了,于是继续喝,继续玩,“围棋赌酒到天明”。
与刘十九一起在这张便条里流传千古的,是红泥小火炉,一到冬天,现代人的朋友圈里,到处都是这句话,都是喝酒的邀约。这是一款什么样的炉子呢?我小的时候家里用过一种煤炉,红土烧制的,褚红色,经不起大的磕碰,应该与诗人家里的大体相同。只是,我们烧的是很多孔眼的蜂窝煤,诗人的燃料应该是木炭。但不管是不是红泥炉,不管是什么燃料,只要有一炉火在,就会生出一怀温暖,生出严冬里的幸福感。
夜晚,四野静寂,除了偶尔一声犬吠,余下的就是簌簌的落雪声。这时候,坐在炉火前,读书也是件开心的事。雪夜闭门读书,在热烘烘的炉火跟前,一页页忘我地读着,看得心潮澎湃,不时地拊掌叫绝,确是人生快事。常有人感叹,文学能有什么用!是的,文学不能帮你买一篓炭,但你看,它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有趣,能慰藉你漫漫雪夜里的孤单寂寞。
我小时候的冬天,最喜欢守在火炉子旁边,看红红的小火苗从蜂窝煤的孔洞里呼呼地跳出来,把小手盖在上面,再迅速移开,烘得热乎乎的。玩够了,就抓一把花生放在环形的炉盖子上,看花生壳的缝隙里渐渐冒出一小股白烟,渐渐地扑出香气来。黄豆放在上面,一会儿就会被烫得直跳;红芋会软烂香甜,玉米粒会开出花来。母亲有时候还会倒腾个“火锅”给我们暖身子,白水里煮上白菜和嫩豆腐,捞出来蘸酱油吃,一屋子雾气缭绕热气腾腾。那些天寒地冻的日子,常常是一家人围坐在炉火前,父亲用芦花编织木底草鞋,母亲缝缝补补,哥哥姐姐做作业,我则抱着炉子,吃得满嘴乌黑。吃饱了,就坐听风声,迅猛的、凌厉的北风扫过干枯的树梢,扫过冰冷的屋瓦,呼啸着疾驰而去。几十年过去,现在回忆起来,仍能感觉到那嗖嗖疾驰的劲风,感觉到炉腔里小火苗轻微的喘息,感觉到“暖老温贫”。
记不清在哪里了,曾看到过这样一段描述:“雪后晴日,温冬酒一壶,卤肉、糟鱼为佐,临窗独酌,闲看顽童呵手堆雪人,不觉日昏,而酒亦尽矣。”这个画面,真让人觉得静日生香,明亮又温暖,觉得作者身后,肯定有一个红泥小火炉旺旺地烧着,小火苗调皮地忽闪跳跃,温着一壶老酒。杯空了,他转过身来,斟上,继续慢饮,继续看窗外的景致,直到天色昏黑。严冬里,只要有一炉火在,时光怎么都是好的,独酌好,对饮好,读书好,闲坐亦好。
都说张爱玲孤傲怪僻,不食人间烟火,她却喜欢看人生煤炉子。寒天清早的人行道上,扇子扇出滚滚的白烟,她就喜欢在那烟雾里走过,那烟雾薰眼而呛人,却是香而暖的,是尘世的味道。说白了,她的骨子里,和我们普通人一样,也贪恋着人间烟火。
只为,那一点点的暖
文/凌波仙子
是要写个前提了,每次提及往事,总是这样来回的涂抹,删除,再重写,我的笔包揽不了太多的记忆,最深刻的一笔,也不知该从哪开始,或许,生活生命中有太多太多值得提及和回忆。在这样的冬日,这样下雪的夜晚,开始怀念老家的红泥小火炉,父亲的烟袋锅子,母亲的针线筐,还有那些爱串门的婶子大娘……
——前记
一,红泥小火炉
第一场雪来临,我驱车赶回老家,车后箱里装着从超市买的取暖器,足浴盆,父母年龄大了,在冬日,越来越怕寒冷。他们越来越卷曲的腰身,犹如老房子一样,经不住风霜雨雪的侵蚀了。
走进院落,就听见厨房里剁饺子馅的声音,那感觉又回到很多年前,每次放学回家,走到家门口,都能听见厨房母亲做饭,碰触碗盆的声音。亲切,温暖,更多的是心里踏实。
厨房的上空有袅袅炊烟,我掂着东西跑进院子,父亲正在忙活,看见我手里买的取暖器,就开始唠叨我,以后别乱花钱了,看现在挣钱多不容易,那洋玩意我们使不惯,还是这泥糊的小火炉实惠,父亲从门后搬出去年的小火炉,腰身开裂了,再用泥巴糊糊,还是一样的好用,我买回的取暖器,不等拆开,父亲又塞进车后厢里。
回到家里,都是遵从老人的意愿,吃过午饭,我便卷起袖子,和父亲在院落里糊起了小火炉,在农家小院落里,和父亲一起分享着他的快乐,他充实的每一天,跟父亲讲着我的工作,我的事情,也听他家长里短的说着村子里发生的事情。掌灯时分,小火炉已经燃起来了,母亲便放上小汤锅,熬煮排骨。
我偎着母亲,小火炉映红了我的脸,暖暖的,静静的。时光总是在某个瞬间,扯着你的思绪回到过去,回到某个时段。
关于小火炉的回忆,我想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不会忘却。通身红泥巴,顶着小汤锅,小水壶,偎着母亲的腿,听着小火炉发出嗤嗤的声音。有时,上面放着未烤熟的红薯和馍片,花生。那种烤出来的香味挑逗着你的味觉,你的口水。在被窝里赖床的我们姐妹,便伸出手臂,向母亲讨要着,嬉闹着。
整个冬天,都是在小火炉的身旁度过,后来去外地求学,赶到放假,便会急急忙忙的往家赶,脑子里一直想着家里的红泥小火炉,想着那个温暖的空间。
其实,这些都是因为想家而惹起的相思。那是因为,想家,想父母亲了。
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很多的片段,那些光阴走过的痕迹,会在你的脑海里打上印记,深深的,不可磨灭。
亦如,这个红泥小火炉,陪伴着我的少时光阴,下雪的日子,只需闭上眼睛冥想,也是暖暖的。
二有种爱叫聆听
回到家里,总是感染着母亲的快乐,偎依着母亲的温暖。其实,你不需多言,只要安静认真的聆听,母亲也是快乐的。
拿回来的足浴盆也没有派上用场,吃过晚饭,母亲就用水壶热了开水,让父亲泡脚,八几年的时候,父亲去密县拉脚,赶上雨雪天,一双脚在雪泥路上整整走了一天一夜,便落下了老寒脚。母亲便每天晚上给父亲烧开水烫脚,春夏秋冬,一日不少。
父亲烫脚的时候,我悄悄的走出房门,把刚买回的足浴盆放在侧房里,母亲服侍着父亲洗脚,对父亲唠叨着,埋怨着,那或许是他们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光,不忍心惊扰,我站在院落里,看见月亮爬上来。
母亲在喊我,急急的声音。把月亮关在门外,我在门内,母亲说,这么冷的天,怎么在外面?我笑着,没有搭话。
我想母亲的快乐不止这些,就像和母亲在一个盆里洗脚,母亲总不忘记她的唠叨,这么些年了,这脚还是这么冰凉,给你做的棉鞋也不穿,那买的皮鞋是好看,但不暖和呀,哪有做的棉鞋这么暖脚的?小时候,最不爱和母亲一起烫脚,怕听她的唠叨,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竟然习惯了她的唠叨,也习惯了和母亲一个盆里烫脚,以至到现在的渴望和想念。
时光最无情,却做着最有情的事情,它让你在不知觉的时候,爱上某种习惯,又在你非常渴望和想念时,把时间刻薄,裁短。
那个夜,和母亲在一个盆里烫脚,母亲唠叨着,东邻药婶家的绵羊该下仔了,竟然死了,别忘记明天起床后去她家买一些羊肉回来,能吃就吃,不能吃就悄悄的扔掉。后院的东子哥,地里种了很多红辣椒,租人摘辣椒,六毛钱一斤,明天呀,我早点过去,一天能挣十几块钱呢。你回去以后,把这取暖器退了,扣点钱没事,以后回来,别乱花钱了,回去空了时间,给我织一件毛衣吧,你给我买的这些衣服,我都放着没穿,这还是那一年,你学织毛线时,给我织的,一直穿着,合身也暖和……
水凉了,续上热水,又凉了,再续……温暖延续着,从脚部开始蔓延,一直到心里,到心里,直到把体内的冰冷逼出体外,逼成一汪湿漉漉的泪。
却原来,我的快乐就是母亲的快乐,而分享母亲的快乐,更是我最大的快乐。
窗外,雪,又开始下了,静悄悄的。
我,和我的家人,和红泥小火炉,在窗内。
温暖的火炉
文/任文
那个年月,山里的冬天很冷,经常下雪。
天刚蒙蒙亮,母亲早起在室外台阶上生火炉。柴火在引燃,木炭在火炉里燃烧,映红了窗户纸。母亲叫醒我,起床,穿衣,洗脸,戴手套,手提火炉,跨出院门去上学。
学校位于一个高出公路几十米的高坡地,我们的教室在一座破庙里。那时,读小学是五年制。庙里的三间教室分为三个班,一三年级一个班,二四年级一个班,五年级单独一个班。庙里的神台就是老师的讲台,长方形黑板就在神台后边,白灰砌成的黑板,学期初用黑墨水刷新一次,往往不到学期末,黑板变成了白板。老师所写的字我们看不清,认不清黑板上写的是“白沟”,还是“白狗”?我们认读生字“白沟”,有个俏皮的学生故意高声读作“白狗”,惹得班里两个年级学生哄堂大笑。老师让他走到黑板前认读,他颤抖着身子向前走了几步,机敏地大声读出“白沟”二字,老师扬起的教鞭缓缓落下,“老师,白字白板我看不清。”老师看看斑驳的黑板,示意他坐回座位。此时,另一年级的学生看到老师的眼神也默不作声了,独自完成自己的作业。
上小学我就爱上了作文课。隔壁班是五年级教室,语文老师朗读大哥哥大姐姐的作文,我们常常偷听失神,课堂老师提问总会闹出笑话。破庙里无顶棚,隔墙的三间教室上空空荡荡,那位老师授课声音高自然听得到。我们班语文老师上《小马过河》,老师提问一个女生,“在妈妈的鼓励下小马试探着过河,他明白了什么?”那位女生回答:“小鸡们在一起争食,他们知道撒在地面上的玉米有数,不抢吃不到。”女生回答,逗得师生都笑了。原来隔壁教室五年级语文老师在朗读学生作文《可爱的小鸡》,难怪会“张冠李戴”。
寒风吹彻的冬日,教室的窗户纸簌簌作响。我们坐在教室里上课,眼睛朝着黑板,双手不由伸向脚下的火炉。偶尔,哪位学生无意间脚踩着了火炉边沿,火炉掀翻,炭火炭灰撒了一地不说,这节课的授课内容就算停止了。老师忙着看炭火是否烧着了学生脚面?无事还好。老师帮学生清理地面,炭火重新放进炉里,火往往就不旺了,直至熄灭。有时刚上课,“嘭”的一声响,引起一片哗然。原来课间学生爆米花,余下的玉米粒此时刚好炸开了,无奈。
说到手提“火炉”,那是家里大人给孩子自制的,大孩子手提的是破旧的瓷盆做的大火炉,小孩子手提的是旧瓷碗做的小火炉。火炉边穿三个对等的洞,用三根长度相等的铁丝固定向上拧在一起,再拧一个手提的小环,提着平稳自如。小学毕业那年,我的手提小火炉换成了旧瓷盆做的大火炉。得益于那红红的火炉的温暖,我的那间小屋墙上贴满了学校老师发给我的一张张奖状,我的作文被老师朗读讲评,放学路上我的身边多了一群小伙伴,他们乐意听我讲所见所闻、编故事。
积雪的日子,脚下咔嚓咔嚓作响,一不小心在雪地里一脚踩空或滑倒,人连火炉一起重重地摔在地上,逗得伙伴们笑得前俯后仰,你追我赶没完没了……
那年月,冬日的雪总是下不完,厚厚的雪覆盖了山川、河流,到处一片白茫茫。从上学到放学,我们都在火炉中度过那段美好的时光。
那年月,我们生火炉用的木炭是生产队按户分配的,往往不够用就完了。父亲为了节省木炭,烧炕时在灰中埋下烧透了的硬杂木柴火碳,第二天早晨好引燃木炭,夹在其间也能当作木炭用。读初中,老师讲解白居易的《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我才对伐木烧炭者的艰辛劳作有了更深的理解。读唐诗,白居易《问刘十七》诗云:“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诗中的意境恬适,回味不尽,那种清新纯朴的泥土气息,让身居钢筋水泥中的我们望尘莫及啊!
如今的孩子多么幸福!家里有取暖设备,上学路上有暖手宝,教室安装取暖的空调。看到这些,怀念提着火炉上学校的年代,那看似不起眼的自制火炉温暖了我的心房,让我有了人生最美好的回味。有火炉的日子,冬天不再寒冷;有火炉的童年,感觉总是那么温暖。
我的北国
文/金越
小村
那一隅荒野,被小村点燃。
阑珊的灯火映照一段往事。
外祖父,在炕沿,我在炕角。
有一抹绿,躲在鸟巢里,若隐若现。绿芽眺望枣花,裹不住的风,一个劲儿往外蹿。
眺望我儿时的憧憬,眺望晨光的鸟鸣,眺望炊烟袅袅的温暖。
村庄,沉下时光的斑驳。
枣花奔跑。
我牙牙学语的北国,吟诵唐诗宋词,韵脚在小村奔跑。炉火、屋角、庭院,鸭鹅鸣叫纠缠不清。
拨开夕阳,拨开云雾,拨开山水,远眺牧童牵着三两头老牛,从暮色中走远。
村夜,喜鹊归巢,坠入村庄的香甜。一觉醒来,黑与白之间,甜与涩之间,一个情节,在生命的版图难捕捉已经模糊了的轮廓。但我怎么也挥不去,村庄柳笛鸣春的模样。
火炉
温暖在往事里缠绕。拖拉机的鸣唱,唤醒了农夫的梦。
稻谷、高粱。
收割一些过年话,收割成熟的菜园,收割我的莽撞。
火舌奔腾。
窗棂上的霜花,捧读一阙宋词。油墨弥散我的天空,书包里跳跃的音符,奏鸣一屋子的咳嗽。
我无法预料。此刻火舌的残喘。我搅动空气,伸出手,想从无形中抓紧万象,抓住花间飞舞的蝴蝶。
我敬畏广袤的土地,仅存的余温炮制整个冬天的足不出户。一阵风袭来,冰释火炉的冷。
老屋厢房溢满过往的月光,火炉蹿出菊花的影,陶公在南山,我在北国,相隔冰天雪地。归去来兮,我的辞章吟咏大雪漫漫。
席卷而来的大雪啊,一幕幕回放,回放风车的影子。
麦田与鸟
我会记住,城市尽头的麦田。
稻草人在招呼。一只鸟吹奏金笛,鸟翅声扑棱棱地响起。因为锤打,因为淬火。镰刀,收割土地的肥沃。
草挣脱羁绊葳蕤了。枯黄。倒地。
空旷。没有麦穗的月光。倾听鸟鸣,世上最完美的天籁。
大鸟与露清欢。
无垠大地。兀自仙乐飘飘。
捧出辽阔,捧出麦穗的孤绝。与鸟并肩而呼。我相信收割之后的旷野和辽阔。我要拔净野草,从北再向北,垄沟里摔打汗珠。
锄禾挥汗如雨。
开垦,开垦,再开垦……
直到我融化一场雪,迎来春天。
云在我身旁
一朵槐花,追逐鸟鸣。
老枝。瓦檐。
我梦中的小山坡,冬天雪盖三层被,瑞雪啊,兆丰年。灶火正旺,从灶窝里飘出来的香,激发我的胃。
田野,阳光有些孤独。生命的底色翻晒了出来。
一碗粥,按照红豆的红,赶赴暮色。
回到云朵,我听到了呜咽的云,积压的大地,一直在战栗。
麦浪没有嗅到,一碗粥飘来的热望。
我在田埂上和高粱比武,在土堆下和小伙伴斗蟋蟀……时光滑过我的指缝,斑驳的痛告发了我。
倔强的眼神抵挡不住我的稚嫩。
攥着拳头 ,咬牙切齿,擦干眸子。
和云朵一起犯傻。可是,一夜的雪绞尽脑汁,吹冷了我的田园和那条奔跑的河流。
老枝。瓦檐。越发孤独。我回不去的村庄,是否有一滴露,打翻了今夜的星辰,漫过城市的街角,到处灯火阑珊。
只有我的心,还在云朵上张望。
教室里的泥火炉
文/米丽宏
小时候的冬天,取暖都是靠火炉。炉子是那种红砖垒砌、黄泥抹缝儿的泥炉子,二尺见方、一米多高、外方内圆,放在讲台里侧。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老师个个都会砌炉子。寒风一起,学校就号召各班砌炉子。同学们被要求一人带一块砖来,泥铲子、泥抹子、麦秸也是学生自己报名带来的。准备工作完成,余下的事就看老师大显身手了。抽中午或大课间,老师脱去外套、挽起袖子,一头汗、两手泥,忙得直冒汗。几个学生在老师的指挥下,一会儿搬砖,一会儿和泥。
有一年,我们班主任是个年轻的女老师,从没做过泥水活儿。砌炉子前,她先到别班教室观摩了整个过程,回来便信心十足地如法炮制。老师累得卷发都贴在额上了,白衬衣上溅了好些个黄泥点子,当然炉子砌得也很漂亮。可那个冬天,我们班的炉子老是不冒火,光吐烟;火灭了,还特别难生着。有次,值日生七点就到校生火,一直到八点十五分上课铃响,还没有把炉火生着。他们一脸的黑灰,两手拿着书在炉口拼命地扇,那炉子一点儿不领情,发脾气似的冒着滚滚浓烟,屋子里云山雾罩一般。老师进来,只听一片咳嗽声,看不见人。于是,我们被轰出教室,在墙根儿站成一排,晒着阳光,互相挤着,呜哩哇啦地背课文。老师从办公室找了两张废弃的油印纸,又让近处的同学跑回家拿了一篮子玉米棒,才引着了火。
平时,如果哪个学生没吃早饭,带块冷干粮来校,老师会准许在火炉上烤烤吃。有时,他还会用自己的水壶为我们烧开水。我们一边做作业,一边听着水壶的吟唱,感觉到的是一种家的气氛。
每年冬天闹流感的时候,学校会购进几缸醋,每班分一些。老师便拿了锅,在教室里不厌其烦地熏醋。据说,醋能杀死感冒病毒,我们那时感冒的人还真不多。